本报记者 王丽丽
开栏的话:
当法治中国的巨轮破浪前行,总有追光者以信仰铸炬、以担当为桨,立起时代的精神标杆。北京金融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第二庭庭长丁宇翔为法而生、以法为命的故事,总能深深触动人们的心弦,给我们力量、赠我们希望、予我们温暖。为深入挖掘丁宇翔的先进事迹,展现新时代人民法官的风采,即日起,本报推出“走近丁宇翔”系列报道,通过记者的采访和记录,我们将探寻他弃高薪入法院的可贵初心,感受其用心定分止争的为民情怀,领略其办大案要案的专业智慧,见证其带病坚守的钢铁意志。听其故事、感其精神、汲其力量,让我们一同走近丁宇翔,与丁宇翔同行。敬请期待。
开栏的话:
当法治中国的巨轮破浪前行,总有追光者以信仰铸炬、以担当为桨,立起时代的精神标杆。北京金融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审判第二庭庭长丁宇翔为法而生、以法为命的故事,总能深深触动人们的心弦,给我们力量、赠我们希望、予我们温暖。为深入挖掘丁宇翔的先进事迹,展现新时代人民法官的风采,即日起,本报推出“走近丁宇翔”系列报道,通过记者的采访和记录,我们将探寻他弃高薪入法院的可贵初心,感受其用心定分止争的为民情怀,领略其办大案要案的专业智慧,见证其带病坚守的钢铁意志。听其故事、感其精神、汲其力量,让我们一同走近丁宇翔,与丁宇翔同行。敬请期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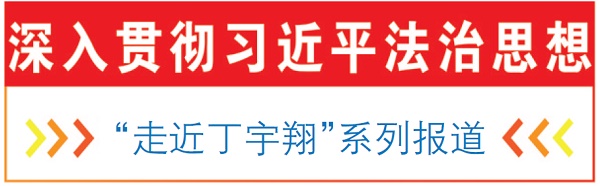
从北方小镇的书桌到北大法学院的殿堂,从田埂间躬身劳作的农家子弟到北京法庭上断案明理的专家型法官,从挺拔健康的体魄到与癌细胞殊死较量,再到最终将病魔击退——丁宇翔四十余年的人生轨迹里,每一步都写着“不容易”。他把所有风霜与荆棘,都化作了腼腆笑容里的温和与坚定。
采访前,记者在心里反复推演措辞:一定要绕开那些与病痛相关的话题,绝不能让提问变成一把钝刀,再去划开他早已结痂的伤口。可当真正坐在他对面时,才发现之前所有的小心翼翼都成了多余。
他身上没有半分“病人”的脆弱标签,语气平静得仿佛医生在解读一份与己无关的病历。那种抽离了个人情绪的淡然,是穿过生死关卡后,把苦难嚼碎咽进心里,最终化作生命底气的通透。
最让人动容的是,他与法学之间深入骨髓的情感。于他而言,法学从不是冰冷的条文,既是寒窗苦读时挚爱的专业、端坐法庭时钟爱的事业,更是健康跌至谷底、被绝望裹挟时,唯一能伸出手救助他的“超能力”。在无数个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入睡的深夜,这份力量给了他对抗黑暗的勇气,让他在绝境里始终能看见光。
黄河岸边,法治初心萌芽
“大学选法律,是经过深思熟虑吗?”
“其实也没有。”
“那是谁定的?”
“我自己。”
丁宇翔回答记者提问时言简意赅。话音落下,又腼腆地补充:“那个时候,和现在不一样。父母不大管我们。”
少年时代的丁宇翔,生活在黄土高原东端的山西忻州。浑浊的黄河水漫过田埂,哺育一望无际的麦田,也滋养着他波澜不惊的孩提时代。
烟火气里满是庄稼的清香。家里没遇过官司,村里没人打过官司,唯一能和“法”沾上边的,是电视里偶尔闪过的庭审画面,或是报刊上印着的法律政策条文。
“依法治国”的春风,恰是在那个世纪之交的节点,吹进这方黄河滋养的土地,悄悄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懵懂的种子。
“我当时就想,报法学专业,社会比较需要,将来也好就业。”丁宇翔回忆起高考前的心路历程,“我的第一志愿专业就是法律,最终被山西大学法学院录取,读国际经济法。”
心中那颗“法律”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,是在踏入大学校园之后。捧着厚厚的法律书反复品读,丁宇翔逐渐意识到:原来那些乡村里“说不清、道不明”的邻里纠纷,那些“靠人情、凭习惯”解决的矛盾,能在这些铅字里找到清晰的答案。
大学四年,最珍贵的一段经历,当属跨越数十个农村的田间调研。1999年夏天,丁宇翔和同学揣着几封介绍信,带着手写的调查问卷,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行程。他们坐着绿皮火车先到县城,下车后常常要徒步十余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,最终走遍了太原、晋中、忻州、运城、临汾地区的三十多个农村。“我们或是住在当地同学家,或是在车站将就过夜,只有在运城住过一次简陋的招待所。”丁宇翔说他们那时年轻,不失眠,到哪里都能倒头就睡。
这段往事,深深地印刻在山西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研究室主任董玉明的记忆中,他对记者说:“丁宇翔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我组织辅导的农村调查项目,通过深入农村调查,提出《关于山西农村法治现状的调查与对策建议》,我作为省政协委员整理该建议后提交提案,受到省委、省政府的重视。在那时,还没有现在的大学生课外科研训练项目,该项目完全是根据教师和学生的愿望自行组织,由教师辅导和资助完成的,实属不易。”
“那是我大学阶段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”丁宇翔的语气里多了几分郑重,“我虽然生在农村,但家乡在平原地区,灌溉方便、条件不算差,此前对农村的了解其实很片面。跑了那么多村子才知道,不同地区的农村,法治意识、纠纷解决方式差异那么大。”
他们精心设计的问卷里,藏着对乡村法治最朴素的探寻。丁宇翔说,也是从那时起,他第一次尝试用研究的视角看待问题,“后来到北大读研究生,包括到现在都喜欢研究问题写写东西,我觉得是从那次调研开始,打开了探索法治问题的那扇门”。
燕园淬炼,锚定法官理想
“对北大,我特别向往。”提及这段求学经历,丁宇翔十分珍视。他说,那时的他常常自问:为何一定要上北大?要去追寻什么?
直到2003年,他终于圆梦北大法学院,成为葛云松教授门下第一位研究生,答案才在三年时光里逐渐清晰。
北大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资料,是他此前从未接触过的“知识宝库”,也为他打开了深入法学世界的大门。而葛云松教授组织的读书会,更成了他法学训练的“核心课堂”——每周要啃完一本法学经典,再接受一场“连环追问”,他手边的《德国民法典》译本等书被翻得书脊开裂,页边贴满密密麻麻的便利贴,记录着思考的痕迹。“每次讨论都超过半天时间,让我真正养成了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。”丁宇翔回忆道,老师的点拨总能让他跳出固有视角,“领悟到看问题的角度原来可以更全面。”
那段时光,史尚宽与王泽鉴两位学者的著作,塑造了丁宇翔对民法学的体系化认知。“史尚宽教授治学极为严谨,著作中对每个概念、规则的论述,都以‘史料考据’为基础,堪称‘民法理论的考据典范’。”而王泽鉴先生的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》,则成了丁宇翔法学方法论的“启蒙书”:“文章结构清晰、文字精练,总能从具体案例出发,把民法处理问题的逻辑讲得透彻。”丁宇翔从中读懂了法学研究共通的思维方式。
研究生二年级下学期,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两个多月的实习经历,让丁宇翔第一次近距离触摸到一线司法实践的脉搏。作为“法官助手计划”的一员,他有机会深度思考案件中的法律问题:撰写简单案件的判决书草稿、旁听法官的庭审,接触的多是民三庭的公司类纠纷,从票据争议到买卖合同,每一个案件都让他感受到写判决书的挑战与价值,感受到定分止争的满满获得感。“特别锻炼人,也让我真切体会到了‘法律落地’的意义。”丁宇翔沉浸在那段回忆中。
“我们那届学生基本都是81、82年左右生人,宇翔比我们大三两岁,有更多社会阅历经验,更显得老成持重,颇有兄长之风。法学系的同学书生意气,叠加少年锐气,无论是社会公共话题,还是班内寝内琐事,都可能各抒己见,争论得不可开交。这时候往往是宇翔高屋建瓴,以理服人,引导大家探索出一个能够兼容的结论,形成彼此能够接受的共识。”丁宇翔的室友刘砺兵现在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,他们在北大期间同住一间寝室。刘砺兵感慨地说:“现在回看,从那时起宇翔就展示出一个优秀的法律实务工作者的素质,不仅是专业素养突出,更难得的是能够以深厚的社会阅历去理解和共情利益纷争的各方,从而创造出一个有助于‘纠纷解决’的空间。”
丁宇翔出众的才华也被职场猎头“盯”上了。半年多后,毕业就业的十字路口如期而至。丁宇翔收到了一家知名律所的录用通知,成为同学中最早拿到录用通知的人。
当得知丁宇翔选择法院而放弃律所后,该律所合伙人特意从巴黎飞回来,与他深谈至晚上11点。丁宇翔早已有所准备——“我不想逃避,就想当面表达抱歉,但在职业选择方面我还想遵从内心的想法。”丁宇翔内心很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
“我还是想当法官。”这个选择的背后,是深思熟虑的考量,“律师通过服务帮助当事人,教授通过学术影响社会,而法官能把专业意见通过生效判决为社会运行提供行为指引。”
在丁宇翔看来,把专业意见融入每一份判决的论证里,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,从中收获的幸福感与价值感,才是自己真正追求的。
法槌之下,生命重获力量
“法官将自己的专业意见融入判决中,给社会运行提供行为指引,这就是法官职业对我的吸引力。”当丁宇翔在北京金融法院的办公室里向记者说出这句话时,他已从2006年入职时的书记员,成长为能以审判树规则、以专业促治理的资深法官。
近二十年的耕耘,他始终坚守着最初的理想——在个案审判中践行司法为民,用专业之力推动社会法治进步。他用一个个标杆性案件,在法治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。
面对低频噪声案,他来到当事人家中,亲身体会“住在这儿会疯掉”的煎熬。他请教中科院、生态环境部的声学专家,甚至邀请民用建筑噪声标准起草人出庭辅助,最终推动裁判思路升级——噪声侵权判定不再仅以国家标准为唯一依据,真正守住了老百姓“安宁生活”的权利。
在全国首例“被遗忘权”案中,他明确当事人可通过“一般人格权”主张未被类型化的个人信息利益,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了关键裁判规则;面对消费者机票信息被诈骗团伙获取的纠纷,他从法理层面破解取证难题,判决航空公司承担侵权责任,用司法实践践行“让该保护的权利真正得到保护”。
面对复杂的群体性纠纷,他找到了兼顾公正与效率的解法。在260余名股民起诉的索赔案中,他牵头推动专业技术公司和高校共同研发“多因子迁移同步对比法”损失核算模型,用更科学的模型核算投资者损失;面对2500件同类案件带来的审判压力,他推动建设“代表人诉讼平台”,历时三个多月攻克无数技术漏洞,最终形成可复制的群体诉讼解决方案,如今已成为证券类群体性案件的标准审理模式。
事业蒸蒸日上时,命运却递来一份残酷的“判决”——CT片上3.8×2.7厘米的阴影,叠加着“肺癌晚期”的诊断,让他和他的家人瞬间坠入冰窟。
妻子张瑞凤心痛地说:“至今不能释然那种‘天塌下来’的恐惧,可宇翔只用两周就调整好心态,还反过来安慰我,‘案子还没办完呢,不会有事儿的’。”
前五个月的重度化疗,丁宇翔挺过来了,肿瘤从“拳头大”缩小到“薄片样”。“之后身体状态好了不少,但情绪不大行,很低落”,丁宇翔说自己努力过了,但真的无法通过医生所建议的养花、弹吉他等方式让自己好过一些。
在家里看来看去、转来转去,他还是拿起了法律书。“是一篇法学论文让我再次体会到法律工作的乐趣”——深夜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时,丁宇翔索性打开电脑梳理写作“证券发行交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”问题,最终论文发表在《中国应用法学》上。“专心做喜欢的事,就忘了病痛,是法律救我于痛苦之中。”
又过了几个月,他感到自己身体状况“已经可以”了,“突破重围”执意回到工作岗位。工作成了最好的“良药”:返回工作岗位两周后,他的睡眠状况和健康指标逐渐好转,他从每晚醒来七八次变成四五次,四个月后血液指标全部正常。
“在北京金融法院,没有一个案子是简单的,但恰恰是这种‘不简单’,最能激发人的斗志。”丁宇翔总说,人的精神状态太重要了——当你满心想着把案子办好、把问题解决,那些缠人的病痛,也就一并“不在话下”了。
法律于他,工作于他,是唤醒生命力的钥匙。如今被问起对抗病魔的经验,他说得格外实在:“我的经验是——能工作,就工作。”
夜幕下的北京金融法院,灯火常明。丁宇翔的身影,始终穿梭在这片光亮里。他不把自己当病人,也不让同事把他当病人,他和大家一起在繁忙的审判岗位上默默奉献。
抬眼望去,窗外车流如河,像极了奔腾向前的“法治长河”。而丁宇翔,就像这长河中一盏澄澈明亮的灯。纵使风雨来袭,始终稳稳矗立,映照公平正义的前行方向,让每一份期盼都能收获公正的回响。
个人简介:
丁宇翔,男,汉族,1978年7月出生,山西忻州人,中共党员,北京大学法学硕士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(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)法学博士。现任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二庭庭长、二级高级法官。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、全国模范法官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2024年度法治人物等荣誉,被评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。
采访前,记者在心里反复推演措辞:一定要绕开那些与病痛相关的话题,绝不能让提问变成一把钝刀,再去划开他早已结痂的伤口。可当真正坐在他对面时,才发现之前所有的小心翼翼都成了多余。
他身上没有半分“病人”的脆弱标签,语气平静得仿佛医生在解读一份与己无关的病历。那种抽离了个人情绪的淡然,是穿过生死关卡后,把苦难嚼碎咽进心里,最终化作生命底气的通透。
最让人动容的是,他与法学之间深入骨髓的情感。于他而言,法学从不是冰冷的条文,既是寒窗苦读时挚爱的专业、端坐法庭时钟爱的事业,更是健康跌至谷底、被绝望裹挟时,唯一能伸出手救助他的“超能力”。在无数个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入睡的深夜,这份力量给了他对抗黑暗的勇气,让他在绝境里始终能看见光。
黄河岸边,法治初心萌芽
“大学选法律,是经过深思熟虑吗?”
“其实也没有。”
“那是谁定的?”
“我自己。”
丁宇翔回答记者提问时言简意赅。话音落下,又腼腆地补充:“那个时候,和现在不一样。父母不大管我们。”
少年时代的丁宇翔,生活在黄土高原东端的山西忻州。浑浊的黄河水漫过田埂,哺育一望无际的麦田,也滋养着他波澜不惊的孩提时代。
烟火气里满是庄稼的清香。家里没遇过官司,村里没人打过官司,唯一能和“法”沾上边的,是电视里偶尔闪过的庭审画面,或是报刊上印着的法律政策条文。
“依法治国”的春风,恰是在那个世纪之交的节点,吹进这方黄河滋养的土地,悄悄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懵懂的种子。
“我当时就想,报法学专业,社会比较需要,将来也好就业。”丁宇翔回忆起高考前的心路历程,“我的第一志愿专业就是法律,最终被山西大学法学院录取,读国际经济法。”
心中那颗“法律”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,是在踏入大学校园之后。捧着厚厚的法律书反复品读,丁宇翔逐渐意识到:原来那些乡村里“说不清、道不明”的邻里纠纷,那些“靠人情、凭习惯”解决的矛盾,能在这些铅字里找到清晰的答案。
大学四年,最珍贵的一段经历,当属跨越数十个农村的田间调研。1999年夏天,丁宇翔和同学揣着几封介绍信,带着手写的调查问卷,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行程。他们坐着绿皮火车先到县城,下车后常常要徒步十余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,最终走遍了太原、晋中、忻州、运城、临汾地区的三十多个农村。“我们或是住在当地同学家,或是在车站将就过夜,只有在运城住过一次简陋的招待所。”丁宇翔说他们那时年轻,不失眠,到哪里都能倒头就睡。
这段往事,深深地印刻在山西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研究室主任董玉明的记忆中,他对记者说:“丁宇翔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我组织辅导的农村调查项目,通过深入农村调查,提出《关于山西农村法治现状的调查与对策建议》,我作为省政协委员整理该建议后提交提案,受到省委、省政府的重视。在那时,还没有现在的大学生课外科研训练项目,该项目完全是根据教师和学生的愿望自行组织,由教师辅导和资助完成的,实属不易。”
“那是我大学阶段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”丁宇翔的语气里多了几分郑重,“我虽然生在农村,但家乡在平原地区,灌溉方便、条件不算差,此前对农村的了解其实很片面。跑了那么多村子才知道,不同地区的农村,法治意识、纠纷解决方式差异那么大。”
他们精心设计的问卷里,藏着对乡村法治最朴素的探寻。丁宇翔说,也是从那时起,他第一次尝试用研究的视角看待问题,“后来到北大读研究生,包括到现在都喜欢研究问题写写东西,我觉得是从那次调研开始,打开了探索法治问题的那扇门”。
燕园淬炼,锚定法官理想
“对北大,我特别向往。”提及这段求学经历,丁宇翔十分珍视。他说,那时的他常常自问:为何一定要上北大?要去追寻什么?
直到2003年,他终于圆梦北大法学院,成为葛云松教授门下第一位研究生,答案才在三年时光里逐渐清晰。
北大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资料,是他此前从未接触过的“知识宝库”,也为他打开了深入法学世界的大门。而葛云松教授组织的读书会,更成了他法学训练的“核心课堂”——每周要啃完一本法学经典,再接受一场“连环追问”,他手边的《德国民法典》译本等书被翻得书脊开裂,页边贴满密密麻麻的便利贴,记录着思考的痕迹。“每次讨论都超过半天时间,让我真正养成了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。”丁宇翔回忆道,老师的点拨总能让他跳出固有视角,“领悟到看问题的角度原来可以更全面。”
那段时光,史尚宽与王泽鉴两位学者的著作,塑造了丁宇翔对民法学的体系化认知。“史尚宽教授治学极为严谨,著作中对每个概念、规则的论述,都以‘史料考据’为基础,堪称‘民法理论的考据典范’。”而王泽鉴先生的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》,则成了丁宇翔法学方法论的“启蒙书”:“文章结构清晰、文字精练,总能从具体案例出发,把民法处理问题的逻辑讲得透彻。”丁宇翔从中读懂了法学研究共通的思维方式。
研究生二年级下学期,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两个多月的实习经历,让丁宇翔第一次近距离触摸到一线司法实践的脉搏。作为“法官助手计划”的一员,他有机会深度思考案件中的法律问题:撰写简单案件的判决书草稿、旁听法官的庭审,接触的多是民三庭的公司类纠纷,从票据争议到买卖合同,每一个案件都让他感受到写判决书的挑战与价值,感受到定分止争的满满获得感。“特别锻炼人,也让我真切体会到了‘法律落地’的意义。”丁宇翔沉浸在那段回忆中。
“我们那届学生基本都是81、82年左右生人,宇翔比我们大三两岁,有更多社会阅历经验,更显得老成持重,颇有兄长之风。法学系的同学书生意气,叠加少年锐气,无论是社会公共话题,还是班内寝内琐事,都可能各抒己见,争论得不可开交。这时候往往是宇翔高屋建瓴,以理服人,引导大家探索出一个能够兼容的结论,形成彼此能够接受的共识。”丁宇翔的室友刘砺兵现在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,他们在北大期间同住一间寝室。刘砺兵感慨地说:“现在回看,从那时起宇翔就展示出一个优秀的法律实务工作者的素质,不仅是专业素养突出,更难得的是能够以深厚的社会阅历去理解和共情利益纷争的各方,从而创造出一个有助于‘纠纷解决’的空间。”
丁宇翔出众的才华也被职场猎头“盯”上了。半年多后,毕业就业的十字路口如期而至。丁宇翔收到了一家知名律所的录用通知,成为同学中最早拿到录用通知的人。
当得知丁宇翔选择法院而放弃律所后,该律所合伙人特意从巴黎飞回来,与他深谈至晚上11点。丁宇翔早已有所准备——“我不想逃避,就想当面表达抱歉,但在职业选择方面我还想遵从内心的想法。”丁宇翔内心很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
“我还是想当法官。”这个选择的背后,是深思熟虑的考量,“律师通过服务帮助当事人,教授通过学术影响社会,而法官能把专业意见通过生效判决为社会运行提供行为指引。”
在丁宇翔看来,把专业意见融入每一份判决的论证里,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,从中收获的幸福感与价值感,才是自己真正追求的。
法槌之下,生命重获力量
“法官将自己的专业意见融入判决中,给社会运行提供行为指引,这就是法官职业对我的吸引力。”当丁宇翔在北京金融法院的办公室里向记者说出这句话时,他已从2006年入职时的书记员,成长为能以审判树规则、以专业促治理的资深法官。
近二十年的耕耘,他始终坚守着最初的理想——在个案审判中践行司法为民,用专业之力推动社会法治进步。他用一个个标杆性案件,在法治进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。
面对低频噪声案,他来到当事人家中,亲身体会“住在这儿会疯掉”的煎熬。他请教中科院、生态环境部的声学专家,甚至邀请民用建筑噪声标准起草人出庭辅助,最终推动裁判思路升级——噪声侵权判定不再仅以国家标准为唯一依据,真正守住了老百姓“安宁生活”的权利。
在全国首例“被遗忘权”案中,他明确当事人可通过“一般人格权”主张未被类型化的个人信息利益,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了关键裁判规则;面对消费者机票信息被诈骗团伙获取的纠纷,他从法理层面破解取证难题,判决航空公司承担侵权责任,用司法实践践行“让该保护的权利真正得到保护”。
面对复杂的群体性纠纷,他找到了兼顾公正与效率的解法。在260余名股民起诉的索赔案中,他牵头推动专业技术公司和高校共同研发“多因子迁移同步对比法”损失核算模型,用更科学的模型核算投资者损失;面对2500件同类案件带来的审判压力,他推动建设“代表人诉讼平台”,历时三个多月攻克无数技术漏洞,最终形成可复制的群体诉讼解决方案,如今已成为证券类群体性案件的标准审理模式。
事业蒸蒸日上时,命运却递来一份残酷的“判决”——CT片上3.8×2.7厘米的阴影,叠加着“肺癌晚期”的诊断,让他和他的家人瞬间坠入冰窟。
妻子张瑞凤心痛地说:“至今不能释然那种‘天塌下来’的恐惧,可宇翔只用两周就调整好心态,还反过来安慰我,‘案子还没办完呢,不会有事儿的’。”
前五个月的重度化疗,丁宇翔挺过来了,肿瘤从“拳头大”缩小到“薄片样”。“之后身体状态好了不少,但情绪不大行,很低落”,丁宇翔说自己努力过了,但真的无法通过医生所建议的养花、弹吉他等方式让自己好过一些。
在家里看来看去、转来转去,他还是拿起了法律书。“是一篇法学论文让我再次体会到法律工作的乐趣”——深夜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时,丁宇翔索性打开电脑梳理写作“证券发行交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”问题,最终论文发表在《中国应用法学》上。“专心做喜欢的事,就忘了病痛,是法律救我于痛苦之中。”
又过了几个月,他感到自己身体状况“已经可以”了,“突破重围”执意回到工作岗位。工作成了最好的“良药”:返回工作岗位两周后,他的睡眠状况和健康指标逐渐好转,他从每晚醒来七八次变成四五次,四个月后血液指标全部正常。
“在北京金融法院,没有一个案子是简单的,但恰恰是这种‘不简单’,最能激发人的斗志。”丁宇翔总说,人的精神状态太重要了——当你满心想着把案子办好、把问题解决,那些缠人的病痛,也就一并“不在话下”了。
法律于他,工作于他,是唤醒生命力的钥匙。如今被问起对抗病魔的经验,他说得格外实在:“我的经验是——能工作,就工作。”
夜幕下的北京金融法院,灯火常明。丁宇翔的身影,始终穿梭在这片光亮里。他不把自己当病人,也不让同事把他当病人,他和大家一起在繁忙的审判岗位上默默奉献。
抬眼望去,窗外车流如河,像极了奔腾向前的“法治长河”。而丁宇翔,就像这长河中一盏澄澈明亮的灯。纵使风雨来袭,始终稳稳矗立,映照公平正义的前行方向,让每一份期盼都能收获公正的回响。
个人简介:
丁宇翔,男,汉族,1978年7月出生,山西忻州人,中共党员,北京大学法学硕士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(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)法学博士。现任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二庭庭长、二级高级法官。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、全国模范法官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2024年度法治人物等荣誉,被评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。


